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值此之际,缅怀战争中牺牲者,反思历史之重是纪念的应有之义。德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5月7日举办的纪念活动中表示,“纳粹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给欧洲及全球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德国对这一历史遗产深感负罪,并承认这一责任。德国将继续肩负起这一责任,铭记历史,并通过实际行动传承这一记忆,特别是在幸存者逐渐减少的今天,牢记历史、警惕未来的责任尤为重要”。然而,当人们将目光转向东亚,难免会发出疑问:作为同为轴心国、侵略国和战败国的日本,在战败八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能否发出如德国那般掷地有声的反思与承诺?
在思考二战的战争责任、大屠杀以及历史认识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会把德国和日本分别作为积极案例和消极案例作比较。但是,长期以来少有中文出版物会从比较的视角讨论这两个国家。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相关的著作,仅笔者有限的了解就有雅斯贝尔斯《罪责论》(2023)、柯兰德《希特勒的恶魔》(2023)、对马达雄《希特勒的逃兵》(2024)等多部作品。然而,仲正昌树的《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2025)稍有不同。仲正是一位专攻德国社会思想史的日本学者,他在战后六十周年(2005年)的时间节点出版该书。通读完全书后留给我的直观印象是:研究对象虽是德国,真正意图却是对日本的深刻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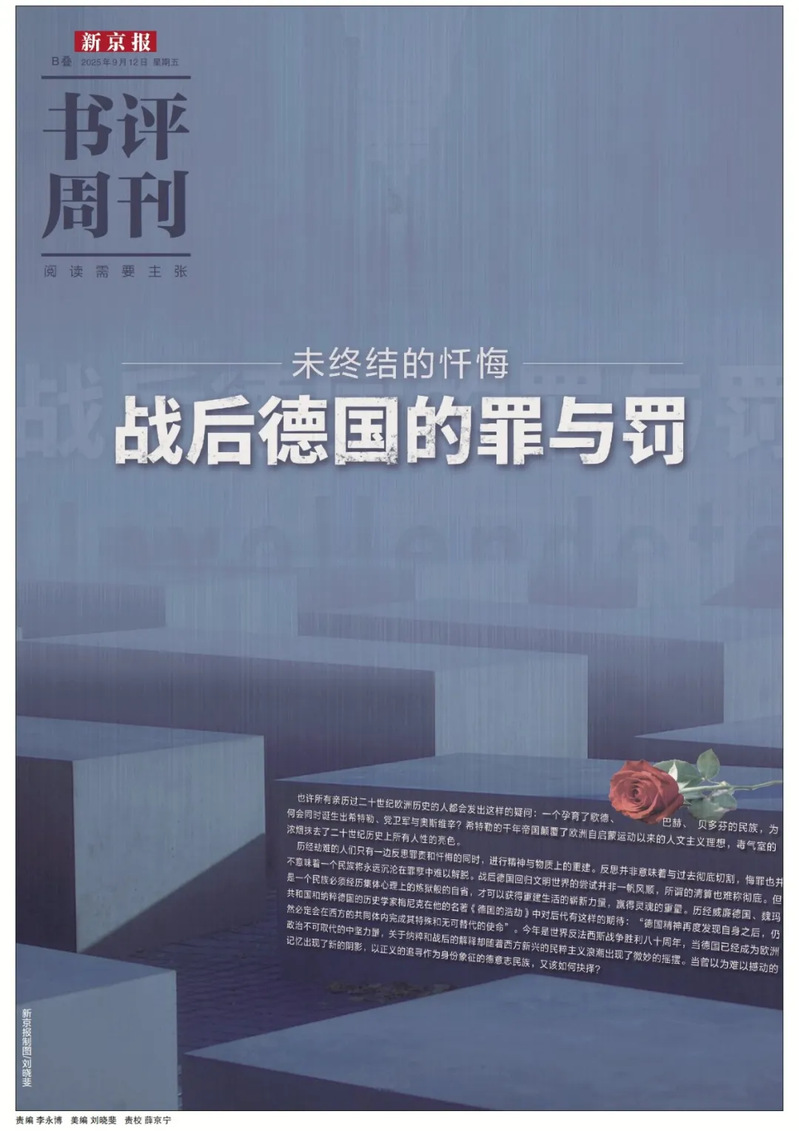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12日专题《未终结的忏悔:战后德国的罪与罚》B06-07。
撰文 | 王广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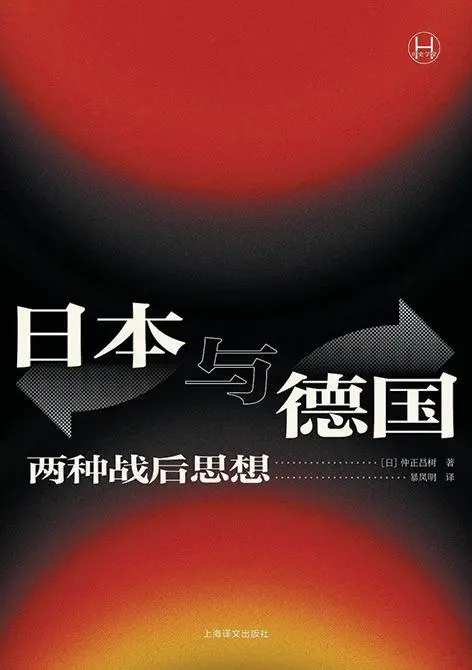
《日本与德国》
作者:(日)仲正昌树
译者:暴凤明
版本:历史学堂|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年6月
从“大恶人 ”到“中等恶人”:战争责任认知的路径差异
仲正在该书开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比喻来说明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战争责任上的不同看法:德国是一个因为犯下极其恶劣的大罪而受到周围彻底追究,从而更好地理解善与恶的原大恶人A,而日本则是与这个大恶人A相比犯下罪行不那么明显,因此受到周围部分追责,最终只具备了不彻底的善恶标准的原中等恶人B(《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第15页,下同)。这是该书中立论的前提,同时作者也指出,这个比喻必然会遭到日本国内左派和右派的批判。
作为国际社会的常识(笔者宁愿把它称为常识,而不是共识),德国在战争责任的问题上反省更加彻底,其虔诚的反省、积极的赔偿以及与周边国家(包括犹太人群体)寻求和解的尝试为国际社会普遍称道;而日本的反省多少有那么一些不情愿,赔偿也十分有限,与周边邻国在历史问题上的龃龉较多。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何日本与德国在战争责任的认识上会呈现这种差异。如果从比较的可能性出发,那么时间、空间、体制以及地区局势可以提供解释两国差异的维度。
就时间维度而言,日本和德国对战争的反省存在鲜明的时间差。战败后的德国,纳粹政权分崩离析,盟军快速占领德国并推行民主化、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等措施;战后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并没有那么及时,正如接下来讨论战争责任时所触及的那样,日本在1945年至1952年处于联合国对日占领军司令部(GHQ)的占领期,日本没有及时认识到对周边邻国的加害责任。同时,丧失外交权的日本也没有可能与周边邻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在日本宣布投降到盟军进驻日本存在至少两周的空窗期,军部在此期间销毁了大量对其自身不利的证据,这也导致后续东京审判过程中取证的困难。

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与影像拍摄者,约翰·马吉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作为人证,控诉日军屠杀暴行。 图/纪录片《东京审判》中1946年东京审判历史影像
就空间维度而言,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既发生在国内,也发生在国外。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家常便饭”,德国国内乃至欧洲境内的人民目睹了犹太人强制收容所的设置以及犹太人被迫害的事实,所以对大屠杀的反省也更加直接;日本的战争罪行主要发生在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日本民众无法体验日军的残暴,这直接导致加害者意识的缺乏。此外,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反而强化了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广岛和长崎位于日本国内,是日本国民作为大战受害者的象征。与日本对东亚国家造成的伤害相比,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对于日本人直观感受来说)更加显著”(第23页)。
仲正在该书第二章花费了较大的篇幅讨论“国家形态”,这与笔者所谓的“体制”维度有相似之处。仲正援引政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的话指出,“德国真是狡猾,把所有战争责任都推给了纳粹”,尽管这句话具有误导性,但是其潜台词是纳粹政权已经被彻底消灭,责任推给纳粹就能够免除个体的责任。从体制层面而言,战败后的德国尽管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但两个国家与纳粹德国完成了“切割”。日本则不然,除了极少数军国主义者遭到审判之外,统揽大权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更重要的是军国主义时期的精英官僚几乎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这也导致战后日本的各项政策与战前甚至战时具有强烈的连续性,日本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称之为“1940年体制”。
就地区局势而言,尽管二战结束后不久便进入所谓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但是德国和日本分别所处的欧洲和东亚地区局势有明显的差别。由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这导致两个德国不得不通过“输诚”的方式争取更多邻国支持其正统性,在对待纳粹大屠杀以及其他战争罪行上也就更坦率(民主德国甚至更进一步,由于其基础是由受到纳粹迫害的共产主义者和抵抗活动家建立的,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和犹太人一样,都是纳粹的受害者)。日本尽管维持着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却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美国介入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让日本摆脱军事要塞化的处境(朝鲜半岛、台湾岛以及彼时尚未回归日本的琉球群岛成为前沿阵地)。日本可以不需要通过“输诚”的方式争取与周边邻国的快速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以及争论主要在国内政治领域(例如保守的自民党和进步的社会党之间),无需在国家间关系的场合过度讨论。仲正在文中援引右翼学者西尾干二对战后德国“狡猾性”的现实主义批判(第4页),而日本又何尝不是呢?

纽伦堡审判现场。 图/1945年纽伦堡审判历史影像,BRITISH PATHé历史影像档案
从“战争责任”到“战后责任”:语义转变背后的政治含义
提到战争责任,便很难回避雅斯贝尔斯对罪责的经典定义,在其名著《罪责论》中,雅斯贝尔斯将罪责分为四类,分别为:法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灵魂(形而上的)罪责。雅斯贝尔斯“罪责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及时性、条理性和政治实用性。及时性体现在这些论述始于二战结束后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的演讲(1945-1946年);条理性体现在他从法律、政治、道德和灵魂四个层面对战争责任问题做出论断,被认为是关于个体以及集体罪责问题分析最为经典的伦理框架之一;政治实用性体现在这些主张逐渐被联邦德国政府付诸实践,对德国战后清算历史,反省战争罪责,促进国民对历史的理解和判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仲正在书中亦将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作为重要参照,考察德国和日本对待战争责任的差异。在有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争论中,经常会出现左翼和右翼的对峙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混乱,仲正认为其原因可能是“战后日本缺乏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能够为辩论提供清晰思路的思想家”。在笔者看来,日本并不是缺少这样的思想家,诸如丸山真男等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在日本战败伊始便抛出“超国家主义”这一对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构造的论断。事实上,丸山真男在战后初期也注意到了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但是并没有将其具象化,丸山本人直接讨论日本对具体受害国的加害责任(罪责)或许是在1950年代后半期。
所以,“战争责任”这一表述在战后初期的日本还不具有加害责任的意涵,而是在考察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时所使用的一种表达,在当时的语境下基本等同于“战败责任”。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为确保军民一体化的国家体制得以延续,尽可能压制舆论对战争责任的讨论。1945年8月28日,皇族首相东久迩亲王在记者会见时首次公开承认日本战败,并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战争力量遭到急剧破坏;联合国对本土的轰炸、原子弹爆炸以及苏联参战;过度的战时统制;国民道义的低下等四条。因此号召“军官民全体进行彻底的反省和忏悔”,这就是战后“一亿人总忏悔”的起源。
仲正认为,如果是任意强调“全民有罪”的集体罪责论,就会像雅斯贝尔斯担心的那样,个人的责任会被掩埋在整体中,从而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战后初期也未必会考虑到对旧殖民地或亚洲国家人民造成伤害的罪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心和批判仍然集中在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等与日本国家制度等根本性问题息息相关的领域,包括战争赔偿问题在内的加害责任并不是他们言论活动的焦点。日本主动提出战争责任并且开始成为一种风尚是在占领结束后的1950年代后半期,这时,在舆论杂志上频频出现针对天皇、军国主义者、知识分子、科学家、文学家甚至日本共产党的战争责任论述。
相较“战争责任”这一直接指向加害的表达,“战后责任”在日本语境中更像是一种消极继承,是在模糊战争罪责基础上对历史记忆的延宕性回应。高桥哲哉在《战后责任论》一书中将其定位为“作为应答可能性的责任”,“战后责任”既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责任,也是一种可视化的责任。也就是说,无论从思想的视角还是行动的视角都是可以做出回应的一种责任。“战后责任”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含糊其辞而导致的,例如,进入1990年代之后成为焦点的“从军慰安妇问题”“731部队细菌实验问题”“民间赔偿问题”等,对于日本政府而言这些问题在经过严肃的调查取证之后是完全可以做出“积极应答”的,或正式道歉、或提供补偿、或建立悼念设施等,但是日本政府的“应答”一直没有让亚洲人民满意。受害者不提出求偿、究责的要求或许是出于“宽容、宽恕”的原则,但不意味着纵容加害者否定战争行为、扭曲历史认知。
思想论争与公共记忆:德国的明辨与日本的糊弄
以德国为坐标来批评日本,是否就意味着战后德国在战争责任抑或说战后责任上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事实上也并不尽然,除了仲正在书中提到德意志民族主义复权的问题之外,对德国的战争责任形成挑战的还有纳粹政权逃兵的恢复名誉问题、国防军的战争罪责问题以及纳粹官僚的问责问题等。
以纳粹政权逃兵的恢复名誉问题为例,对马达雄在《希特勒的逃兵》一书中指出,希特勒统治期间因为不满纳粹统治而成为逃兵的德国人仍然难以逃脱法庭的判决,“逃兵”的标签不仅让他们难以获得应得的抚恤,甚至还要承受德国人的冷眼嘲笑。对马并不认为战后初期的德国人天然就有明确的罪责意识,反而是抱有强烈的挫败感,毫无自我反省的意识,不承认正是德国人自己孕育出了希特勒的独裁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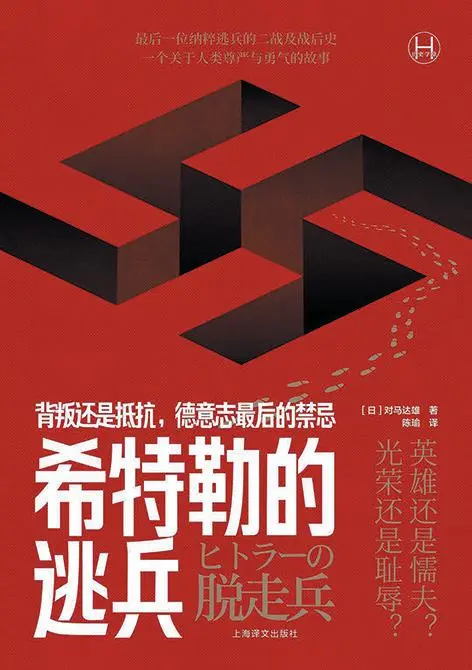
《希特勒的逃兵》
作者:(日)对马达雄
译者:陈瑜
版本:历史学堂|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年12月
这些被遮蔽的、被刻意隐藏的以及被忽视的与纳粹有关的一切最终都得到了比较公允的解决,在笔者看来,其背后至少得益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德国左翼政党的牵制;德国思想界的论争;市民团体的不懈斗争。
1969年德国社会党党首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就任联邦德国总理,终结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垄断地位。勃兰特上台后积极推行“东方政策”,显著改善了同东欧国家的关系。1970年,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的“惊世之跪”不仅缓和了同犹太人的关系,还将德国国内对纳粹政权的反省带入新高度。
自纳粹政权崩溃之后,德国思想界并不乏围绕纳粹政权以及战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争论,其中尤以19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最具代表性。仲正指出,这场辩论虽然出现“历史学家”几个字,但是其内容并不限于历史学的方法论或者关于历史事实认定方法的技术性讨论,而是围绕如何基于已知历史事实,理解自己国家“历史观”的相关问题。尽管在这次辩论中,部分保守派历史学家试图通过修正主义的历史叙述将纳粹大屠杀解释为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是就事实本身而言,任何否定大屠杀、为纳粹正名的言论都不被允许存在。

《浪潮》(2008)剧照
相较而言,市民团体的斗争更具有持续性和战斗力,在前述纳粹逃兵的问题上,1990年成立的“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为纳粹逃兵复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国防军无罪论”(意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正规武装部队——国防军声称没有参与犹太人大屠杀和大量战争罪行,并将其犯下的种种暴行与责任推给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党卫队)的主张直到1995年才经由汉堡社会研究所巡回举行的《国防军展览》而有所动摇,该展览展示了国防军犯下战争罪行的1380张图像记录,引发德国公众的集体思辨以及对此说法的重新审视。
在德国,真理愈辩愈明;在日本,历史却愈辩愈模糊。基于上文提到的三大势力的努力,让我们来看看战后日本政治生态和言论活动空间的演变吧。尽管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国内都存在所谓“保守革新对立”的格局,但是作为革新政党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从来都没有掌握过政权,这让日本与邻国的关系修复更多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而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
在思想界,虽然也存在主张的差异,但是却少有论争。仲正在该书中提到的加藤典洋和高桥哲哉关于“历史主体”的论争算是其中代表性的论争。在关于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的立场上,加藤主张首先应该让“左”和“右”两方均为日本的战死者哀悼,之后再作为“日本国民”向全亚洲的战死者表示哀悼。而高桥则批评加藤论述中隐藏的民族主义,是以对亚洲死者的哀悼为借口,试图美化本国战死者,甚至将导致他们死去的民族主义也合理化。
不过,加藤与高桥的论争并没有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其中很重要的背景在于冷战结束后左翼势力的集体式微,日本的市民团体也好、知识精英也罢,已经很难左右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上向历史修正主义方向的滑坡。进入1990年代以后,“从军慰安妇”问题、强征劳工问题浮出水面,但是日本政府对待该问题的立场却十分暧昧。河野洋平以官房长官谈话(1993年)的方式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后来却遭到日本国内保守政府(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的强烈反弹。

《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剧照。
二十年过去,一切都变了吗?
转眼间,该书日文原版出版至今又过去了20年,相较于德国,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特征是对历史修正主义的容忍度大大放宽。自1993年以来,历代日本首相均会在每年8月15日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上以“深刻反省”和“哀悼”等表述提及对亚洲邻国的加害责任。安倍晋三在2012年再次执政以后,自2013年起便不再提及对战争加害的反省,而是专注于本国人民的受害。
笔者的研究发现,当前日本对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论的宽容度越来越高,放在三十年前的1990年代,如果日本阁僚因为南京大屠杀的失言,往往会面临被迫辞职的结局,而如今,即便在公开场合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高层也不会有被迫辞职的风险,甚至还能够收割民粹主义者的支持(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名古屋前市长河村隆之便是鲜活的例子)。
在日本战败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以及七十周年的时候,时任日本首相均发表了首相谈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村山谈话”(1995),最具争议性的则是“安倍谈话”(2015)。“安倍谈话”中提到,“不能让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关系的子孙后代背负不断谢罪的宿命”,这一意在回避战争责任、与历史相切割的表态颇受日本保守派欢迎。在此背景下,任何挑战这一叙事的尝试都面临着较大的政治风险。
由于十年前的“安倍谈话”以非常暧昧的方式回避了战争责任,在时值战败八十周年的2025年,日本国内对于是否发表首相谈话十分慎重。石破茂在今年年初的一次场合释放信号,有意在8月15日发表“石破谈话”,但是遭到自民党内以及舆论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八十年过去,德国在忏悔与和解中一步步重塑其国际形象,而日本则在历史修正主义的漩涡中逐渐滑向遗忘与回避。此时此刻,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未曾完成历史清算的国家,能否真正走向未来?历史并未结束,答案仍需我们共同守望。
